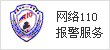【游记】拉卜楞寺游记
创建时间:2017-04-12 阅读(2925)
2017年4月初的甘南之旅,虽一直未见诸于文字,但它留给我的记忆,至今还是那样清晰,一如昨日。回想起拉卜楞寺、花湖、郎木寺、若尔盖大草原、九曲黄河。。。。。。那情景犹如一幅幅画卷,历历在目。我多想用画来描绘那画一般的风景,我多想用诗来描述那诗一般的意境,可惜力不从心,我从来没有像这次写甘南一样煞费周章。也许是太想写好,生怕不能准确地记述这次旅行的精彩吧,我始终觉得敲击键盘的手好沉、好沉,脑中一片混沌,无法从纷乱的思绪中理出头绪。我不得不翻出当时的照片,边看边回忆,驱使思绪牵引着心境,重新回到去年的那一时、那一刻。
一觉醒来,明显睡眠不足的大脑昏昏沉沉,十分散乱,依稀记得红酒、佛教、小吃、仓央嘉措。。。。。。当时唯独不记得这里已经是高原,甘南的夏河。按道理初到高原,应该禁酒、早睡,但身心却如同出笼的鸟儿一般,兴奋不已,天南地北海阔天空一通胡诌八扯,入睡时早已不是昨夜,而是今晨了。 撩开窗帘,看了一眼外面的天,似乎还判断不出阴晴。以日出与否来决定起床的时间,这是我多年外出养成的习惯。每次住宿,我都会选择窗边的床位,以便观察天气,一旦天气适合摄影,立即起身。对日出的期待使我无法重新入睡,渐渐褪去睡意的双眼让我透过朦胧看清了我的住房。这是一间藏式的房间,全木结构,原木原色,隐隐散发着天然的香气,所谓的床其实就是北方汉族的炕,上面放着独具藏族特色的红漆描花小炕桌,把小屋隔成了双人间。我之所以喜欢木屋,一来因为它透着质朴,二来它更加贴近大自然。唯一不喜欢也不习惯的就是不隔音,卧房、浴室、公厕莫不如此。当第二次撩开窗帘时,我几乎惊叫出来。不知何时,太阳已经从东山顶上探出了笑脸。我一骨碌爬起来,用最快的速度穿好衣服、叫醒同伴、拎起相机,风也似地蹿出了门。拉卜楞寺已经从梦中醒来,而我却恍然刚刚入梦,刚刚踏进一个传说中的国度。蓝天映衬着白塔,空中飞翔着鸽群,村庄升起袅袅炊烟,和煦的阳光洒在白塔上,洒在庙宇上,洒在错落有致的屋顶上,也洒在长长的转经路上。拉卜楞寺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的藏民们沿着长长的转经路,转经的转经,朝着拉卜楞寺的方向磕头的磕头,神情专注而虔诚,丝毫不为外境所扰。我置身其间,仿佛就是一个透明人,连自己都觉得如此唐突地出现,与这里浓厚的宗教氛围是那样地格格不入。
穿过成群结队转经的藏民,我爬上后山的一处“制高点”,从那里,可以俯瞰整个拉卜楞寺。 拉卜楞寺是藏传佛教格鲁派六大寺院之一,自1709年创建至今,已经成为包括显、密二宗的六大学院、108属寺和八大教区的综合性大型寺院,形成了独特的藏传佛教文化,包括建筑、学院、法会、佛教艺术、藏经等,被誉为“世界藏学府”。鼎盛时期,僧侣达到4000余人。这里还是甘肃省佛学院的所在地。严格地讲,拉卜楞寺并非单指某一座寺院,而是泛指这一片建筑群。有意思的是,它并不是封闭于高墙大院之内,而是散落在民居中。不知这是否与释迦牟尼“凡圣同居”的理念暗合。
大乘佛教认为,所有的世界都是佛的净土。我们所在的世界就是释迦牟尼佛的净土,本质上完全清净,被称之为“娑婆世界”。但娑婆世界地面高低不平,充满污秽,充满罪恶,没有一点点其他佛土的清净相。佛祖之所以降临秽土,是以慈悲为怀,为要吸引那些满怀贪嗔痴、欲爱为本的众生来到这个世间,以便度化他们。虽身处浊世,但心净则佛土净,质若本洁,自然会如青莲一般出淤泥而不染。
晨钟暮鼓,惊醒世间名利客;佛号经声,唤回苦海迷梦人。站在高坡上,俯瞰拉卜楞寺,触景生情,不由人不发出这样的感慨。由于居高临下,白塔、寺庙、僧人、转经路、转经人都进入了我的“摄程”。透过镜头,我看到的是一幅幅感人的场景:转经路上,身披红袍的僧人,健步如飞的壮年藏民,头裹围巾的藏族妇女,还有白发苍苍的藏族阿爸阿妈。老人手拄拐杖,踽踽而行,在阳光低角度照射下,在地上拖出长长的阴影。
每每见到佝偻着身躯、颤颤巍巍、力不从心、表情木讷的老人,我都会心生悲悯,自然而然地想起佛教中所说的“老苦”。人生即苦。艰难地分娩到世间是苦,伤筋动骨病魔缠身是苦,病痛而死是苦,与亲人生离死别是苦,不得不与厌恶憎恨的人相处是苦,求而不得是苦,欲望炽盛而焚心更是苦上加苦。受了一辈子苦,到老还是不能颐享天年,还要经受“老苦”的折磨。看着他们风烛残年老态龙钟的样子,内心总不免悲哀,他们的现在,不正是自己的未来吗?人生苦短,即使长命百岁,谁又能躲得过老来之苦这一劫呢?
拉卜楞寺有一条环形的转经路,其中很长一段是转经廊,墙壁上安放着不计其数的转经筒。走在长廊里,手摇转经筒,仿佛步入了仓央嘉措那首著名的情诗所描述的情境,“那一月,我转动所有经筒,不为祈福,只为触摸你的指尖”。以前卒读,脑海中曾浮现过诗中描述的意境,而此时,曾经的心有所感却在这里与仓央嘉措撞了个满怀,情景交融,竟令我生出几分感动。据说当年仓央嘉措的足迹也曾遍及甘肃、青海,此刻,谁又能说我脚下的土不是当年仓央嘉措足下的路呢?
仓央嘉措的这首诗流传很广,但据专家考证,并非出自他手,而是后人假仓央嘉措之名而写的“伪作”。且不管学术之争孰是孰非,这样的情诗之所以可以广泛流传,自有它流传的道理。就文字而言,它并不华丽,但“文章做到极处,无有他奇,只是恰好”。就诗意而言,诗句并不仅只是“触摸你的指尖”,而是触碰到了人们的心尖。当想象中的情境与现实的情境恰好吻合时,就会产生一种感觉,这种感觉,就叫作奇妙。当你不经意间邂逅诗情,得以亲身体验那诗句的含义时,你会觉得那诗写得是那样贴切,那样浪漫!
“住进布达拉宫/我是雪域最大的王/徜徉在拉萨街头/我是世间最美的情郎”,这就是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的自画像。他是西藏历史上颇有争议的人物,就连他的生卒时间和地点至今也还都是个谜。有人说他是成功的诗人,失败的活佛,从他留存于世的诗歌中也不难体会出他是个怎样纠结的人:“自恐多情损梵行/入山又怕误倾城/世间安得双全法/不负如来不负卿”。真真愁肠百结百结愁肠!他的一生,都在情天恨海中沉浮,在出世入世间挣扎、彷徨。
当然,仓央嘉措的才情也是毋庸置疑的。“我用世间所有的路/倒退/从哪儿来/回到哪儿去/正如/月亮回到湖心/野鹤奔向闲云/我 步入你……”诗情画意在他的笔下挥洒得淋漓尽致。
转经路上的藏民络绎不绝,有古铜色脸庞的藏族汉子,也有脸上布满风霜的藏族妇女;有拄着拐杖的老阿妈,也有稚气未脱的孩童。在转经路上,见到一位灰头土脸的小姑娘,看上去也就十岁左右,在家人的陪伴下沿着转经路一步一步磕着长头。我不忍心将镜头对准她弱小的、沾满污渍的身躯,只能向她投去怜惜的目光。城里的孩子,十来岁正是无忧无虑穿着新衣裳撒娇耍赖的花季,而她却已经超出自己的承受能力,在飞扬的尘土中匍匐,遭如此罪,受如此苦。我总也想不明白,她们的命运为什么会是这样?
“假使百千劫,所作业不亡。因缘会遇时,果报还自受”。佛教宣扬因果报应,认为人的命运并非天定,而是由自身的业力所致,以善恶诸业为因,能招致不同的善恶果报。正如俗话所说,种瓜得瓜,种豆得豆;善有善报,恶有恶报;有前因必有后果,自作必自受。但这样的说法对她们公平吗?如此说来,这些在今生受苦受难的人,都是因为前世造了恶业,所以才会招致今世的惩罚吗?
也许正是为了让自己的后世不再蒙受她们今生的苦难,她们才如此虔诚地信佛修行吧。因为她们坚信,大慈大悲的菩萨能够救苦救难,帮助他们斩断尘缘,斩断苦根,脱离苦海,惟其如此,才不致堕入轮回。但轮回之苦,是人世间不争的事实,即使拥有坚定的信仰,也无法掩盖苦的本质。换言之,苦并不会因为信仰而变甜。对芸芸众生而言,苦从本质上是 相同的,不同的,只是对待苦的态度和应对苦的方式。
浪子终于为自己的鲁莽和愚昧付出了惨痛的代价。一向任性胡为的他,在一次酗酒后,为争夺情人与人殴斗,不幸死于非命。而当他再次转世时,由于前世恶业深重,他罪有应得地轮回为一只乌鸦,尽管他想用喑哑的嗓音倾诉自己无尽的悔恨与思念,但他的父母已再也无法与之相认。望着年迈的父母日渐衰老的背影,他未语泪先流。前世今生,虽非阴阳两隔,但早已形同陌路。
佛教相信六道轮回,认为“一切世界始终生灭,前后有无,聚散起止,念念相续,循环往复,种种取舍,皆是轮回”。人根据累世所积的业力,在三善道“天、人、阿修罗”、 三恶道“畜生、饿鬼、地狱”这六道中轮回。之所以会周而复始,皆因“一切众生从无始际,由有种种恩爱贪欲,故有轮回”,“当知轮回,爱为根本”,“欲因爱生,命因欲有”,“爱欲为因,爱命为果” 。。。。。。而生死轮回最最根本的,还是缘起无明。在被称为三恶业的“贪嗔痴”中,贪与嗔,又有哪一项不源于痴愚呢?
问:“狗子还有佛性也无?”师曰:“无”。问:“上至诸佛,下至蝼蚁,皆有佛性,狗子为甚么却无?”师曰:“为伊有业识在”。
佛教故事中也有五百大雁听闻佛法,悟道后化为五百罗汉的传说。当然,这样的故事信则有,不信则无。但我向来认为,世界是多元的,三千大千世界,并不唯人独尊,人有人世间,狗有狗世间,鸟有鸟世间,虫有虫世间。。。。。。而且一定都有各自的语言,只是相互之间一时无法破解,无法听懂而已。但这并不妨碍众生平等,和谐共处。如果佛祖真能普度众生,那么无论人也好,狗也好,不都终会殊途同归吗?
当我正忙不迭地捕捉拉卜楞寺美景时,一位身着绛红色僧袍的小师父来到了我的身旁。不知是来朝拜的还是到此出家,身边还有两个家人模样的人陪伴左右。他手里拿着一部数码相机,东拍西照,如果不是一身僧侣打扮,与时尚达人无异。当手机、电脑、数码相机、摩托车、汽车这些现代玩意儿与僧人的古老、神秘、庄重组合在一起时,总让人感觉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。由此我推测,现代僧人的修行要远比古代僧人的修行难度大得多得多,毕竟那些现代玩意儿中,充斥了太多太多的诱惑。要做到清静无为,不起心动念,谈何容易啊。
小师父眉清目秀,一表人才,淡淡一笑,满脸腼腆,给人以绝对的亲近感。每逢遇到这些出家人,我总十分好奇他们的身世,为什么要出家,但总也不好意思打探人家的隐私。我猜想,除了个别本具慧根佛缘的人,大多数男女剃度为僧削发为尼,背后都有一段辛酸的、鲜为人知的故事。可是,世上事,了犹未了,并不会因为他们出家一走了之就可以一了百了。这种难言之隐,恐怕会深埋在他们心底,伴随他们终生。也许,也正因为有如此厚重的铺垫,他们才更易悟透、悟空吧。
小师傅侧身站在山坡上,长长的僧袍随风摆动,当他回首望向山下围着白塔转经的人群时,神色凝重,那身姿透出一种“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”的毅然决然和义无反顾,让我不禁想起了地藏菩萨的誓愿:地狱不空,誓不成佛;度尽众生,方证菩提。
拉卜楞寺和其他众多的佛教寺庙一样,供奉着不计其数的佛像。有的硕大无比,有的精巧玲珑,有的冷酷威严,有的和蔼慈祥,但我起初并不理解人们为什么要耗费巨资建造这么多佛像。正如大彻大悟之人以佛的口吻说道,“你求名利,他卜吉凶,可怜我全无心肝,怎出得什么主意;殿遏烟云,堂列钟鼎,堪笑人供以泥木,空费了多少钱财”。说到底,造像无非都是石身泥胎。求佛,何须向身外求,必得明心见性方成正果。但从理论上讲,供奉佛像有两种意义,一是纪念,二是观想。纪念意义就是见到诸佛的形象,联想佛是思想、智慧、慈悲功德的化身,生起敬仰心,并从佛像的象征意义,得到精深丰富的哲理启示,思想境界得到升华。观想意义就是修禅定的人,眼观佛像,一心向佛,排除杂念,获得入定成就。从实质上来讲,佛教其实是一种信仰、一种心理寄托、一种偶像崇拜。反过来说,信仰实质上也是一种宗教。
细想起来,在全世界范围内,除了朝鲜,像中国这样的无神论国家好像并不多,要么是基督教,要么是伊斯兰教,要么就是佛教,中国好不容易有一个土生土长的道教,还被边缘化了,影响力十分有限。虽然宗教被马克思认定为“精神鸦片”,但一个有信仰的民族总比一个没信仰的民族更有凝聚力。
拿佛教来说,它主张“诸恶莫作,诸善奉行”,这就是一个最基本的道德规范。如果一个国家、一个民族、一个地区的人民可以自觉地信守,国家何愁不安定,民族何愁不和谐,人民何愁不能安居乐业?当然,现在很多人信佛,目的并不纯粹。有的是求解脱,有的是求平安,有的是求富贵,有的是求姻缘,五花八门,无奇不有,甚至连贪官污吏、杀人越货之徒都跑来抱佛脚。但凡此种种,都充满了功利色彩。殊不知佛也不能免定业、不能度无缘、不能救度所有众生。其实,学佛、信佛的根本,还在于启迪智慧,点亮人生,走好自己的路。
傍晚,犹如飞沙走石般来去匆匆的游客已经散尽,尘埃落定,佛门又恢复了它原本的清净。暮色中的佛殿经堂是那样地静谧、安详,为尘世众生忙碌一天的佛陀此时也微阖双目,轻缓地舒了一口气。最后一缕夕阳消失在了经幡竿顶,深蓝色的天空上不时有寒鸦鸣叫着飞过,拉卜楞寺愈发显得幽静和神秘。伫立在寺前小广场,听着塔顶风铃叮咚,看着经幡舞动,我深深地陶醉于这种氛围中。日归西,雀归巢,问心归何处?
一觉醒来,明显睡眠不足的大脑昏昏沉沉,十分散乱,依稀记得红酒、佛教、小吃、仓央嘉措。。。。。。当时唯独不记得这里已经是高原,甘南的夏河。按道理初到高原,应该禁酒、早睡,但身心却如同出笼的鸟儿一般,兴奋不已,天南地北海阔天空一通胡诌八扯,入睡时早已不是昨夜,而是今晨了。 撩开窗帘,看了一眼外面的天,似乎还判断不出阴晴。以日出与否来决定起床的时间,这是我多年外出养成的习惯。每次住宿,我都会选择窗边的床位,以便观察天气,一旦天气适合摄影,立即起身。对日出的期待使我无法重新入睡,渐渐褪去睡意的双眼让我透过朦胧看清了我的住房。这是一间藏式的房间,全木结构,原木原色,隐隐散发着天然的香气,所谓的床其实就是北方汉族的炕,上面放着独具藏族特色的红漆描花小炕桌,把小屋隔成了双人间。我之所以喜欢木屋,一来因为它透着质朴,二来它更加贴近大自然。唯一不喜欢也不习惯的就是不隔音,卧房、浴室、公厕莫不如此。当第二次撩开窗帘时,我几乎惊叫出来。不知何时,太阳已经从东山顶上探出了笑脸。我一骨碌爬起来,用最快的速度穿好衣服、叫醒同伴、拎起相机,风也似地蹿出了门。拉卜楞寺已经从梦中醒来,而我却恍然刚刚入梦,刚刚踏进一个传说中的国度。蓝天映衬着白塔,空中飞翔着鸽群,村庄升起袅袅炊烟,和煦的阳光洒在白塔上,洒在庙宇上,洒在错落有致的屋顶上,也洒在长长的转经路上。拉卜楞寺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的藏民们沿着长长的转经路,转经的转经,朝着拉卜楞寺的方向磕头的磕头,神情专注而虔诚,丝毫不为外境所扰。我置身其间,仿佛就是一个透明人,连自己都觉得如此唐突地出现,与这里浓厚的宗教氛围是那样地格格不入。
穿过成群结队转经的藏民,我爬上后山的一处“制高点”,从那里,可以俯瞰整个拉卜楞寺。 拉卜楞寺是藏传佛教格鲁派六大寺院之一,自1709年创建至今,已经成为包括显、密二宗的六大学院、108属寺和八大教区的综合性大型寺院,形成了独特的藏传佛教文化,包括建筑、学院、法会、佛教艺术、藏经等,被誉为“世界藏学府”。鼎盛时期,僧侣达到4000余人。这里还是甘肃省佛学院的所在地。严格地讲,拉卜楞寺并非单指某一座寺院,而是泛指这一片建筑群。有意思的是,它并不是封闭于高墙大院之内,而是散落在民居中。不知这是否与释迦牟尼“凡圣同居”的理念暗合。
大乘佛教认为,所有的世界都是佛的净土。我们所在的世界就是释迦牟尼佛的净土,本质上完全清净,被称之为“娑婆世界”。但娑婆世界地面高低不平,充满污秽,充满罪恶,没有一点点其他佛土的清净相。佛祖之所以降临秽土,是以慈悲为怀,为要吸引那些满怀贪嗔痴、欲爱为本的众生来到这个世间,以便度化他们。虽身处浊世,但心净则佛土净,质若本洁,自然会如青莲一般出淤泥而不染。
晨钟暮鼓,惊醒世间名利客;佛号经声,唤回苦海迷梦人。站在高坡上,俯瞰拉卜楞寺,触景生情,不由人不发出这样的感慨。由于居高临下,白塔、寺庙、僧人、转经路、转经人都进入了我的“摄程”。透过镜头,我看到的是一幅幅感人的场景:转经路上,身披红袍的僧人,健步如飞的壮年藏民,头裹围巾的藏族妇女,还有白发苍苍的藏族阿爸阿妈。老人手拄拐杖,踽踽而行,在阳光低角度照射下,在地上拖出长长的阴影。
每每见到佝偻着身躯、颤颤巍巍、力不从心、表情木讷的老人,我都会心生悲悯,自然而然地想起佛教中所说的“老苦”。人生即苦。艰难地分娩到世间是苦,伤筋动骨病魔缠身是苦,病痛而死是苦,与亲人生离死别是苦,不得不与厌恶憎恨的人相处是苦,求而不得是苦,欲望炽盛而焚心更是苦上加苦。受了一辈子苦,到老还是不能颐享天年,还要经受“老苦”的折磨。看着他们风烛残年老态龙钟的样子,内心总不免悲哀,他们的现在,不正是自己的未来吗?人生苦短,即使长命百岁,谁又能躲得过老来之苦这一劫呢?
拉卜楞寺有一条环形的转经路,其中很长一段是转经廊,墙壁上安放着不计其数的转经筒。走在长廊里,手摇转经筒,仿佛步入了仓央嘉措那首著名的情诗所描述的情境,“那一月,我转动所有经筒,不为祈福,只为触摸你的指尖”。以前卒读,脑海中曾浮现过诗中描述的意境,而此时,曾经的心有所感却在这里与仓央嘉措撞了个满怀,情景交融,竟令我生出几分感动。据说当年仓央嘉措的足迹也曾遍及甘肃、青海,此刻,谁又能说我脚下的土不是当年仓央嘉措足下的路呢?
仓央嘉措的这首诗流传很广,但据专家考证,并非出自他手,而是后人假仓央嘉措之名而写的“伪作”。且不管学术之争孰是孰非,这样的情诗之所以可以广泛流传,自有它流传的道理。就文字而言,它并不华丽,但“文章做到极处,无有他奇,只是恰好”。就诗意而言,诗句并不仅只是“触摸你的指尖”,而是触碰到了人们的心尖。当想象中的情境与现实的情境恰好吻合时,就会产生一种感觉,这种感觉,就叫作奇妙。当你不经意间邂逅诗情,得以亲身体验那诗句的含义时,你会觉得那诗写得是那样贴切,那样浪漫!
“住进布达拉宫/我是雪域最大的王/徜徉在拉萨街头/我是世间最美的情郎”,这就是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的自画像。他是西藏历史上颇有争议的人物,就连他的生卒时间和地点至今也还都是个谜。有人说他是成功的诗人,失败的活佛,从他留存于世的诗歌中也不难体会出他是个怎样纠结的人:“自恐多情损梵行/入山又怕误倾城/世间安得双全法/不负如来不负卿”。真真愁肠百结百结愁肠!他的一生,都在情天恨海中沉浮,在出世入世间挣扎、彷徨。
当然,仓央嘉措的才情也是毋庸置疑的。“我用世间所有的路/倒退/从哪儿来/回到哪儿去/正如/月亮回到湖心/野鹤奔向闲云/我 步入你……”诗情画意在他的笔下挥洒得淋漓尽致。
转经路上的藏民络绎不绝,有古铜色脸庞的藏族汉子,也有脸上布满风霜的藏族妇女;有拄着拐杖的老阿妈,也有稚气未脱的孩童。在转经路上,见到一位灰头土脸的小姑娘,看上去也就十岁左右,在家人的陪伴下沿着转经路一步一步磕着长头。我不忍心将镜头对准她弱小的、沾满污渍的身躯,只能向她投去怜惜的目光。城里的孩子,十来岁正是无忧无虑穿着新衣裳撒娇耍赖的花季,而她却已经超出自己的承受能力,在飞扬的尘土中匍匐,遭如此罪,受如此苦。我总也想不明白,她们的命运为什么会是这样?
“假使百千劫,所作业不亡。因缘会遇时,果报还自受”。佛教宣扬因果报应,认为人的命运并非天定,而是由自身的业力所致,以善恶诸业为因,能招致不同的善恶果报。正如俗话所说,种瓜得瓜,种豆得豆;善有善报,恶有恶报;有前因必有后果,自作必自受。但这样的说法对她们公平吗?如此说来,这些在今生受苦受难的人,都是因为前世造了恶业,所以才会招致今世的惩罚吗?
也许正是为了让自己的后世不再蒙受她们今生的苦难,她们才如此虔诚地信佛修行吧。因为她们坚信,大慈大悲的菩萨能够救苦救难,帮助他们斩断尘缘,斩断苦根,脱离苦海,惟其如此,才不致堕入轮回。但轮回之苦,是人世间不争的事实,即使拥有坚定的信仰,也无法掩盖苦的本质。换言之,苦并不会因为信仰而变甜。对芸芸众生而言,苦从本质上是 相同的,不同的,只是对待苦的态度和应对苦的方式。
浪子终于为自己的鲁莽和愚昧付出了惨痛的代价。一向任性胡为的他,在一次酗酒后,为争夺情人与人殴斗,不幸死于非命。而当他再次转世时,由于前世恶业深重,他罪有应得地轮回为一只乌鸦,尽管他想用喑哑的嗓音倾诉自己无尽的悔恨与思念,但他的父母已再也无法与之相认。望着年迈的父母日渐衰老的背影,他未语泪先流。前世今生,虽非阴阳两隔,但早已形同陌路。
佛教相信六道轮回,认为“一切世界始终生灭,前后有无,聚散起止,念念相续,循环往复,种种取舍,皆是轮回”。人根据累世所积的业力,在三善道“天、人、阿修罗”、 三恶道“畜生、饿鬼、地狱”这六道中轮回。之所以会周而复始,皆因“一切众生从无始际,由有种种恩爱贪欲,故有轮回”,“当知轮回,爱为根本”,“欲因爱生,命因欲有”,“爱欲为因,爱命为果” 。。。。。。而生死轮回最最根本的,还是缘起无明。在被称为三恶业的“贪嗔痴”中,贪与嗔,又有哪一项不源于痴愚呢?
问:“狗子还有佛性也无?”师曰:“无”。问:“上至诸佛,下至蝼蚁,皆有佛性,狗子为甚么却无?”师曰:“为伊有业识在”。
佛教故事中也有五百大雁听闻佛法,悟道后化为五百罗汉的传说。当然,这样的故事信则有,不信则无。但我向来认为,世界是多元的,三千大千世界,并不唯人独尊,人有人世间,狗有狗世间,鸟有鸟世间,虫有虫世间。。。。。。而且一定都有各自的语言,只是相互之间一时无法破解,无法听懂而已。但这并不妨碍众生平等,和谐共处。如果佛祖真能普度众生,那么无论人也好,狗也好,不都终会殊途同归吗?
当我正忙不迭地捕捉拉卜楞寺美景时,一位身着绛红色僧袍的小师父来到了我的身旁。不知是来朝拜的还是到此出家,身边还有两个家人模样的人陪伴左右。他手里拿着一部数码相机,东拍西照,如果不是一身僧侣打扮,与时尚达人无异。当手机、电脑、数码相机、摩托车、汽车这些现代玩意儿与僧人的古老、神秘、庄重组合在一起时,总让人感觉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。由此我推测,现代僧人的修行要远比古代僧人的修行难度大得多得多,毕竟那些现代玩意儿中,充斥了太多太多的诱惑。要做到清静无为,不起心动念,谈何容易啊。
小师父眉清目秀,一表人才,淡淡一笑,满脸腼腆,给人以绝对的亲近感。每逢遇到这些出家人,我总十分好奇他们的身世,为什么要出家,但总也不好意思打探人家的隐私。我猜想,除了个别本具慧根佛缘的人,大多数男女剃度为僧削发为尼,背后都有一段辛酸的、鲜为人知的故事。可是,世上事,了犹未了,并不会因为他们出家一走了之就可以一了百了。这种难言之隐,恐怕会深埋在他们心底,伴随他们终生。也许,也正因为有如此厚重的铺垫,他们才更易悟透、悟空吧。
小师傅侧身站在山坡上,长长的僧袍随风摆动,当他回首望向山下围着白塔转经的人群时,神色凝重,那身姿透出一种“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”的毅然决然和义无反顾,让我不禁想起了地藏菩萨的誓愿:地狱不空,誓不成佛;度尽众生,方证菩提。
拉卜楞寺和其他众多的佛教寺庙一样,供奉着不计其数的佛像。有的硕大无比,有的精巧玲珑,有的冷酷威严,有的和蔼慈祥,但我起初并不理解人们为什么要耗费巨资建造这么多佛像。正如大彻大悟之人以佛的口吻说道,“你求名利,他卜吉凶,可怜我全无心肝,怎出得什么主意;殿遏烟云,堂列钟鼎,堪笑人供以泥木,空费了多少钱财”。说到底,造像无非都是石身泥胎。求佛,何须向身外求,必得明心见性方成正果。但从理论上讲,供奉佛像有两种意义,一是纪念,二是观想。纪念意义就是见到诸佛的形象,联想佛是思想、智慧、慈悲功德的化身,生起敬仰心,并从佛像的象征意义,得到精深丰富的哲理启示,思想境界得到升华。观想意义就是修禅定的人,眼观佛像,一心向佛,排除杂念,获得入定成就。从实质上来讲,佛教其实是一种信仰、一种心理寄托、一种偶像崇拜。反过来说,信仰实质上也是一种宗教。
细想起来,在全世界范围内,除了朝鲜,像中国这样的无神论国家好像并不多,要么是基督教,要么是伊斯兰教,要么就是佛教,中国好不容易有一个土生土长的道教,还被边缘化了,影响力十分有限。虽然宗教被马克思认定为“精神鸦片”,但一个有信仰的民族总比一个没信仰的民族更有凝聚力。
拿佛教来说,它主张“诸恶莫作,诸善奉行”,这就是一个最基本的道德规范。如果一个国家、一个民族、一个地区的人民可以自觉地信守,国家何愁不安定,民族何愁不和谐,人民何愁不能安居乐业?当然,现在很多人信佛,目的并不纯粹。有的是求解脱,有的是求平安,有的是求富贵,有的是求姻缘,五花八门,无奇不有,甚至连贪官污吏、杀人越货之徒都跑来抱佛脚。但凡此种种,都充满了功利色彩。殊不知佛也不能免定业、不能度无缘、不能救度所有众生。其实,学佛、信佛的根本,还在于启迪智慧,点亮人生,走好自己的路。
傍晚,犹如飞沙走石般来去匆匆的游客已经散尽,尘埃落定,佛门又恢复了它原本的清净。暮色中的佛殿经堂是那样地静谧、安详,为尘世众生忙碌一天的佛陀此时也微阖双目,轻缓地舒了一口气。最后一缕夕阳消失在了经幡竿顶,深蓝色的天空上不时有寒鸦鸣叫着飞过,拉卜楞寺愈发显得幽静和神秘。伫立在寺前小广场,听着塔顶风铃叮咚,看着经幡舞动,我深深地陶醉于这种氛围中。日归西,雀归巢,问心归何处?

.jpg)
.jpg)
.jpg)